2009 (57)
2010 (55)
2011 (83)
2012 (66)
2013 (88)
2014 (102)
2015 (497)
2016 (457)
2017 (603)
2018 (637)
2019 (816)
2020 (701)
2021 (540)
2022 (880)
2023 (542)

今天分享的这篇文章是《写作人:天才的怪癖与死亡》的后记。作者哈尔维·马里亚斯用放大镜在才华里寻找古怪,试图用别具一格的角度,打破我们对那些久负盛名的大作家们的刻板印象。
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精通多国语言,他长期生活在法国,跟莫泊桑这帮人感情非常好,与福楼拜的友谊直到晚年也丝毫不减。下文刻画了福楼拜和屠格涅夫这对挚友晚年的部分生活事迹。同样作为19世纪鼎鼎有名的作家,屠格涅夫性情爽朗外放,每日有花不完的精力,而福楼拜却内向刻苦,日常陷入在纠结而内耗的折磨中。
这两个性格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人,却成为了朋友,他们最常交流些什么呢?
老年人的娱乐
文 | [西]哈维尔·马里亚斯
歌手波琳·维亚尔多——又名加西亚——曾与伊凡·屠格涅夫交好多时,但对他的态度始终不冷不热 (俄罗斯作家本人对她倒是十分殷勤,曾提议将俩人的情侣关系升级成夫妻关系。但维亚尔多太太从未彻底离开过维亚尔多先生) 。她有一次曾经评价伊凡·屠格涅夫为“人类之最悲哀者”。
屠格涅夫与他的挚友福楼拜之间有着长达十七年的深厚友谊,若波琳·维亚尔多有机会对后者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也许她就会把这个评价送给这位《包法利夫人》的作者,而非自己那个备受挫折的失意恋人了。
01
福楼拜时常闭门不出
屠格涅夫热爱旅行
如果读过两位作 家的《 书信集》,读者会感觉到,与波琳·维亚尔多的描述正相反,至少从俩人的通信来看,“人类之最悲哀者”却更像一个世俗、世故、热衷都市生活,甚至有点轻浮的人。
而与此同时,福楼拜只在他故乡鲁昂附近的克鲁瓦塞的家中闭门不出,顶多去巴黎和他的同辈们相聚几日,或去阿尔卑斯山度几个星期假,领略一番“与我们这样的人不相称”、“对我们来说过于庞大而不实用的存在”。
与此同时,屠格涅夫却像一只动作敏捷的松鼠一般在欧洲四处乱窜,从莫斯科、巴登-巴登、柏林、苏格兰、牛津或圣彼得堡等各个不同的地方给他的朋友寄信。其中有些旅行有正经目的,比如去处理财务问题或去领取某个荣誉博士学位,但其他的旅行则纯粹只为打发时间:他会参加一些贵族组织的猎鹧鸪和松鸡的活动,这些贵族热衷打猎,手指总是蠢蠢欲动地想扣在扳机上。

屠格涅夫与福楼拜
而福楼拜却宁可把时间都花在硬啃那些浩瀚无限的书卷上,他唯一的爱好就是整理自己的那些小说和短篇故事集,像是为了完成一项功课。由于他每每需要花费数小时、数日、数周甚至数月才能写出一个能令自己满意的章节,他所拥有的闲暇时间确是所剩无几。
在他的信中,他频繁地抱怨自己的写作工作: 有时候,他会在书桌前耗费十来个钟头陷入纠结,试图解决自己给自己设置的障碍,但最终离成文仍是遥遥无期。在《布瓦尔与佩居榭》写到一半的时候,他曾绝望地计算过,自己已经花了两年时间,依然没有摆脱书中那些愚蠢的人物。
而 屠格涅夫则与他 相反:他很少在信中聊自己是何时、如何写出那么多有待出版的作品的,而且在写作之余他竟还能找到时间把他朋友的作品翻译成俄语。
02
福楼拜致屠格涅夫 :
我们这样的挚友,见面实在太少啦

改编自福楼拜同名小说《包法利夫人》
但在这部书信集中最动人的,还是福楼拜对他的旅人朋友的那些温柔的责备。
在信中,他批评屠格涅夫来访得不够频繁。后者不是因为被痛风所折磨,就是因为要去猎松鸡 (或者要去陪维亚尔多,甚至要去参加某些聚会) ,而屡屡推迟既定的克鲁瓦塞之行,古斯塔夫·福楼拜则对此深表遗憾,他在信中严厉地批评道:
“尽管您日程繁忙,但我只求您来陪我一个下午。而且我相信这不会是您最后一次这样对我。”
或者他会说:
“您不能想象我在思想上的孤单……全世界只有一个人能与我相谈甚欢,而那个人就是您!所以请您保重,不要再像之前那样令我失望。”
甚至是堂堂正正地严词责备:
“您在数月以前就保证会来看我,而您却屡屡食言;就算偶尔来访,我本以为总算能与您相伴一阵子了,您却又没过多久便再次离去。不,不,这样很不好。”
在他去世前几个月,他甚至对屠格涅夫这样说过。
“像我们这样关系非比寻常的挚友,竟然只见过寥寥数面,这太愚蠢了。”
而实际上,福楼拜自己也不愿意出门,而且很不合作。他很讨厌去巴黎旅行。1879年,西班牙人为穆尔西亚遭受洪灾的灾民募集捐款,在巴黎组织了一场慈善聚会,邀请福楼拜参加时他是这样回复的:“我不会仅仅为了一些西班牙人而去巴黎跑一趟的,那样太愚蠢了。”他对自己的一个朋友说得更加明确:为了摆脱此事,他号称自己既不会跳博莱罗舞,也不会弹吉他 (时至今日,穆尔西亚人仍因此事而对这位知名作家怀恨在心) 。
然而,屠格涅夫似乎不是出于无礼或恶意而故意要摆架子。当他终于来到克鲁瓦塞时,他与福楼拜聊个没完,还耐心地听他长篇累牍地朗读自己正在创作的篇章。在周游世界之余,他还不断地通过铁路运输给福楼拜邮寄各种纪念品。俩人曾连续往来了四五封信件,讨论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寄给法国作家(福楼拜)的一件俄罗斯睡袍,这些信件堪称全书中最动人的篇章之一。
福楼拜 写道:
“等我看到那件著名的睡袍时,我估计会感激到流泪的。”
屠格涅夫 回复道:
“我曾希望能够到克鲁瓦塞把这件睡袍亲手交给您……请告诉我您是否收到了。”
当这件著名的睡袍终于送到福楼拜手里时,他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比他写任何政治评论或文学作品时都更热情洋溢:
“这件服饰令我陷入了对专制政权及穷奢极欲的生活的遥想之中。我想赤身穿上它,摇身一变成切尔克斯人。尽管眼下暴风雨肆虐,天气十分闷热,我还是立即穿上了它。”
说不定在亨利·詹姆斯那次著名的拜访中,他穿的睡衣就是这一件。当时,福楼拜穿着睡衣接待亨利·詹姆斯,引发了巨大的丑闻。詹姆斯认为穿这样的服装待客简直是伤风败俗,由此他认定福楼拜的作品一定同样地可憎,因为毫无疑问,它的作者所有事情都是穿着睡衣做的。这样的人还有什么药可救呢?
03
屠格涅夫致 福楼拜:
寄给您的鱼子酱丢了,真遗憾
我们可以注意到,福楼拜与屠格涅夫很少在信中谈到文学 (他们既不讨论自己的作品,也不讨论别人的) 。
在俩人的书信往来中最有趣、最引人入胜的段落多少都和他们日常的家务事有关。确实,在相识之初,为巩固信任,俩人曾不遗余力地互相吹捧。但事实上,即便在友谊日渐稳固之后,他们仍出自本能地互相赞美。
“多伟大的艺术啊!”一个人会说。
“多了不起的心理描写!”另一个人说。
“多么坚定的力量啊!”俩人异口同声地说。
他们时不时地会对左拉评头论足,议论他那些古怪的观点,同时不怀好意地对他的失败悄悄表示幸灾乐祸。

改编自屠格涅夫同名小说《白静草原》
屠格涅夫给他的朋友寄去过一套《战争与和平》,面对如此大部头的书册,福楼拜一开始表示懒得读,之后,他充满热情地读完了前两个部分,但对第三部分多有诟病。据他表示,最后这个部分愧对杰作之名。
他曾生气地评价道:
“情节重复,充满哲学思辨。”
而对于自己的弟子莫泊桑,福楼拜不太爱读他的作品,却喜欢津津有味地听他讲他那些惊人的冒险故事。
1877年的一天,福楼拜十分敬佩地写道:
“莫泊桑在最近给我的信中提到,他在三天时间内做爱十九次!”
“这很好,但我怀疑这样下去他会把自己的精子榨干的。我的好朋友啊,我们可做不了这样的事儿!”
当时,两位好友已年近六十,尽管在有些方面,俩人对自己的年龄仍能一笑置之 (“前几天,一个来自布雷斯特的家伙因暴力侵犯自己的三个女儿和一个十六岁的儿子,在坎佩尔被罚作苦役。这是什么体力!想必我俩可没有这么厉害的体能”) ,但在有些时刻,他们仍能感受到死神临近的脚步。
屠格涅夫写道:
“我的状况糟糕极了……我感觉如此苍老无力,疲惫不堪,备受痛风的折磨,一片昏暗而忧郁的阴影降临到我头上,仿佛在给予我们某种警告……这些瞬间就像死神给我们寄来的问候卡片,好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它。”
如果对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来说,痛风是他最大的敌人 (他在约有八成信件中翻来覆去地提到此事) ,福楼拜则对自己的时代深感不满,并想尽力避免智力退化。但我们都知道,有时候怕什么就来什么。
“我对一切都感到厌烦,尤其讨厌我自己。有时候,我会觉得自己正在变成一个痴呆,脑子里像一个空的啤酒瓶一样空空如也,什么都想不出来。”

电影《希望的另一面》
福楼拜比屠格涅夫年轻三岁,却比他早了三年去世。屠格涅夫晚年在去世前备受病痛折磨,有一次他甚至请求莫泊桑下次来看他时给他带一把自尽用的手枪。但就在福楼拜去世前的六个月,俩人还兴致勃勃地往来了数封信件,讨论屠格涅夫通过铁路运输寄送的一个新的邮包。
福楼拜写道:
“慷慨的人儿啊,我还没有收到您寄的鱼子酱和三文鱼。您是通过哪个邮政通道寄出这两个罐头的?焦灼的情绪啃噬着我的胃呢。”
屠格涅夫闻言开始担心:
“真遗憾三文鱼丢了,它那么美味。”
但最后,包裹还是顺利抵达了,状态良好,福楼拜 说:
“昨晚我收到了罐头。三文鱼真是棒极了,鱼子酱更是令我陶醉到大喊出声。我们什么时候能一起享受这些美味?……您要知道,我几乎不配面包都能吃掉这些鱼子酱,就像吃果酱似的。”
俩人没能再次聚在一起共享美味。事实上,他们从来都是聚少离多。但读着俩人的通信,我们仿佛能感觉到他们最终实现了屠格涅夫的提议——那一次,他曾出于不祥的预感,忧郁地对福楼拜说:
“是的,哎!我们都已经老了,我的朋友啊!这点不可辩驳!”
“至少,我们要像老年人那样自娱自乐。”
本文节选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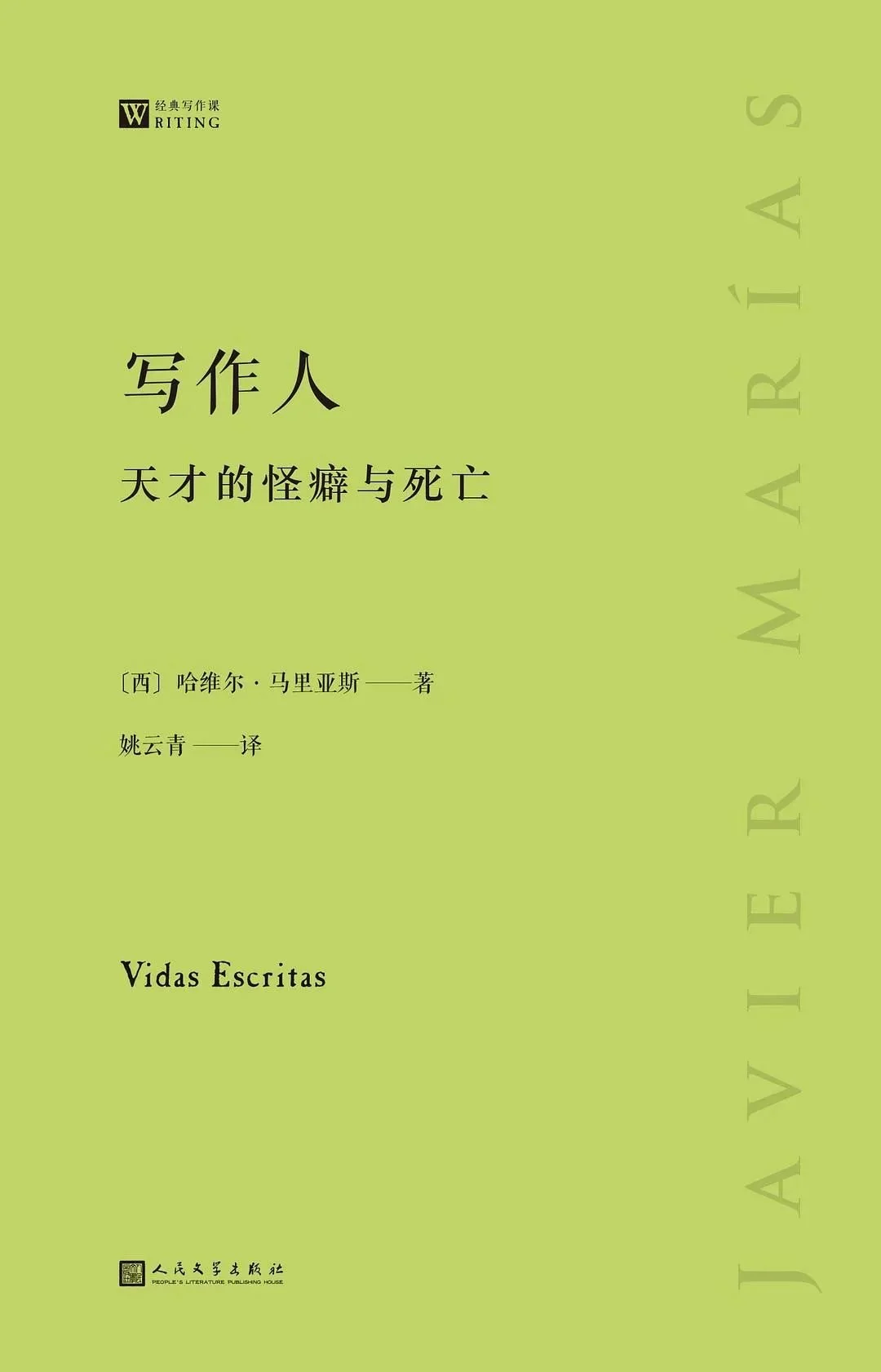
《写作人:天才的怪癖与死亡》
作者:[西]哈维尔·马里亚斯
译者:姚云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