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t
听一段文字,听一首歌...
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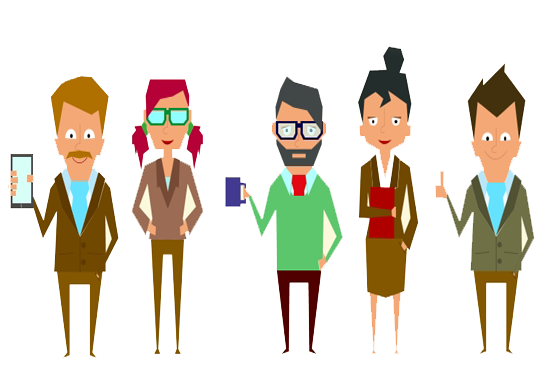
|
|
《减去十岁》 文:谌容 诵:张筠英&瞿弦和
一个小道消息,像一股春风在办公楼里吹拂开来: “听说上边要发一个文件,把大家的年龄都减去十岁!” “想的美!”听的人表示怀疑。 “信不信由你!”说的人愤愤然拿出根据,“中国年龄研究家经过两年的调查研究,又开了三个月专业会议,起草了一个文件,已经送上去了,马上就要批下来。” 怀疑者半信半疑了: “真有这样的事!?那可就是特大新闻啦!” 说的人理由充足: “年龄研究会一致认为:“文革十年,耽误了大家十年的宝贵岁月。这十年生命中的负数,应该减去……” 言之有理! 半信半疑的人信了: “减去十岁,那我就不是六十一,而是五十一了,太好了!” “我也不是五十八,而是四十八了,哈哈!” “特大喜讯,太好了!” “英明,伟大!” 和熙的春风,变成了旋风,顿时把所有的人都卷进去了: “听说了吗? 减去十岁!” “千真万确,减去十岁!” “减去十岁!” 人们奔走相告。 离下班还有一小时,整幢楼的人都跑光了。 六十四岁的季文耀回到家,一进门就冲厨房大喊:“明华,你快来!” “怎么啦?”听见丈夫的声音,方明华忙跑了出来,手上还拿着摘了半截的菠菜。 季文耀站立在屋子当中,双手叉腰,满面春风。听见妻子的脚步声,他腾地扭过头来,两眼放出炯炯的光芒,斩钉截铁地说: “这间屋子该布置布置了,明天,去订一套罗马尼亚家具!” 方明华惊疑地走上前去,压低了声音问道: “老季,你疯了。就那么几千块存款,全折腾了,赶明儿……” “嗐,你知道什么!”老季脸红脖子粗地叫道,“我们要重新生活!” 儿子、女儿不约而同从各自的房间跑了出来,爸爸高声的宣言他们都听见了:这怎么回事,老头子又发什么神经? “去,去,没你们的事!”老季把探头探脑的儿子、女儿轰走了。 然后,他关上门,一反常态,跳上两步,抱住了老伴胖乎乎的肩膀。这几十年不曾有过的亲昵之举,比宣布买罗马尼亚家具更令老伴惊悸。她心想: 这人准是出了毛病! 这些日子为年龄过线、必须退下来的事,搞得他愁眉苦脸的。别说大白天没有这种表示热乎的举动,就是夜晚在床上也是自顾自唉声叹气,好像身边没这个人似的。今天这是怎么啦,六十岁的人了,学起电视剧里的镜头来,羞得她满面通红。 老季呢,他可啥也没觉得,一双眼睛像着了火,一个劲儿地在燃烧。他把木呆呆的老伴半搂半抱地拖到藤椅边,双手按她坐了下去,脸挨着她的耳朵,喜声喜气地小声说: “告诉你一个绝密消息,马上就要发一个文件,我们的年龄都要减去十岁!” “减—十—岁?”方明华手里的菠菜掉了地,两个大眼珠几乎瞪了出来,“我的妈! 真的呀?” “就是真的呀! 马上就要发文件了……” “哎呀! 我的妈呀! 亲娘呀!”方明华“蹭”地站起,自己也不知怎么回事,双手抱住老伴瘦骨嶙峋的肩膀,就在那长长的颊上亲了一个短促的吻。这一着把她自己也吓着了,简直回归到三十年前了。老季略一愣神,拉起妻子的双手,两人连连在房中央转了三圈儿。 “哎哟,头昏,头昏!”直到方明华挣脱手,直拍厚厚的胸脯,才停止了这可能持续下去的快乐的旋转。 “怎么样?小华,你说我们该不该买它一套罗马尼亚家具?”老季理直气壮地望着显得年轻了的老伴。 “该!”她那一双大眼睛里闪烁着熠熠的光辉。 “我们该不该重新开始生活?” “该,该!”她颤悠悠地应声,眼角渗出了泪珠儿。 老季一屁股坐在了小沙发上,闭了一会儿眼,脑子里五光十色的想法如潮水般涌来。忽地,他睁开眼,毅然决然地说: “当然,个人的生活安排还是小事,主要是又有十年工作的机会。这回要好好干它一场了。机关里松松垮垮,要狠狠抓一下。后勤工作也要抓,办公室主任的人选本来就不合适。那个司机班,简直是老爷班,要整顿……” 他挥舞着胳膊,狭长的眼里放着不可遏制的兴奋的光芒: “班子问题需要重新考虑。现在是不得已,矮子里拔将军。张明明这个人,书呆子一个,根本没有领导经验。十年,给我十年,我要好好弄一个班子,年轻化就要彻底年轻化,从现在的大学生里挑。二十三、四岁,手把手地教它十年,到时候……” 小华对班子的重新配备兴趣不大,她憧憬着未来的美好生活。 “沙发,我想,也换换。” “换嘛,换成套的,时髦的。” “床,也要换一个软的。”她脸红了。 “完全正确,睡了一辈子木板床,也该换个软的开开洋荤了。” “钱……” “钱算什么!”季文耀高瞻远瞩,豪情满怀,“主要是多了十年时间哟,唉,这是花多少钱也买不来的呀!” 两人正说得情投意合、神采飞扬之际,女儿忽然推开了一条门缝,问道: “妈,晚上吃什么呀?” “啊,你随便做吧!”方明华心不在焉,早已把吃饭的事忘了个精光。 “不!”老季手一挥,宣布道,“今天出去吃烤鸭,爸爸请客。你和你哥哥先去占座,我和你妈随后就到。” “啊!”女儿张开了小嘴,见父母喜气洋洋的样子,也就没多问,忙去叫哥哥。 兄妹俩忙着去烤鸭店,一路议论。哥哥说,可能是爸爸破格留任。妹妹猜,可能是爸爸提了级,拿到一笔什么钱。当然,他们谁也不可能猜到,减去十岁是比任何级别、官职都可贵千倍、万倍的啊! 家里老俩口的谈兴正浓。 “小华,你也该修饰修饰。减去十岁,你才四十八嘛。” “我? 四十八?”方明华做梦似地喃喃着,一种久已消失了的青春的活力,在她肥胖松弛的躯体里跳动,使她简直昏昏地不知所措了。 “明天去买件春秋大衣,米色的。”老季用批判的眼光打量着老伴紧绷在身上的灰制服,果断地、近乎抗议地说,“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时髦时髦?看着吧,吃完饭我就去买件意大利式夹克衫,就像那个张明明穿的一样。他今年也四十九了嘛,他能穿,我就不能穿!” “对!”方明华拢了拢满头失去光泽、干枯蓬散的花白头发说,“把头发也染染,花点钱去一趟高级美容店。哼,这些年轻人说我们保守,退回十年,我比他们还会生活呢……” 老季一跃站了起来,高声应道: “对,要会生活。我们要去旅游。庐山、黄山、九寨沟,都要去,不会游泳也去望望大海。五十来岁,正当年,唉,我们哪,以前真不会生活。” 方明华顾不上感叹,自个儿盘算着说:“这么说来,我减去十岁,才四十九,还可以工作六年,我也得回机关去好好干。” “你……”季文耀显得迟疑。 “六年,六年,我还可以工作六年。”方明华还在兴奋中。 “你嘛,你就不要工作了。”季文耀终于说,“你的身体不好……” “我身体很好。” 这一刻,方明华跃跃欲试,确实觉得自己身体很好。 “你又去上班,家里这一大堆事交给谁?” “请个保姆嘛。” “啊唷,现在这安徽帮,工作极端不负责任,把这个家交给她们怎么放心!” 方明华也有点犹豫了。 “再说,已经退下来就不要再给组织上增加麻烦了嘛,咹?如果退下来的老同志都要回去,那,那,那不就乱了吗?”季文耀想着不由得打了个寒噤。 “不行,我还有六年时间,我还能干。”方明华坚持说,“你要是不让我回局里,我可以调换工作。找个什么公司去当个党委书记,或者副书记,怎么样?” “这个……现在这些公司五花八门,太杂。” “杂,才要加强领导嘛,做思想政治工作,还得靠我们这些老家伙。” “那好吧。” 老季的点头,就好像是组织部长同意了似的,方明华快乐地叫了起来: “那可太好了! 这个研究会真是知人心啊! 减去十岁,从头开始,连做梦都没有想到啊!” “想到了,我想到了,连做梦都想到了!”季文耀又振奋起来,慷慨激昂地叫道,“文化大革命夺去了我十年青春。十年,十年哪,能干多少事情? 白白地浪费了,只留下一头白发,一身疾病。这个损失,谁来补偿?这个苦果,凭什么要我来吞咽?还我青春,还我十年,这个研究会干得好,早就该这么干了。” 方明华怕勾起丈夫对往日痛苦的回忆,忙笑着把话扯开: “好了,走,吃烤鸭去!” 四十九岁的张明明心里不是滋味。是喜?是忧?是甜?是苦?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好像什么滋味都有,什么滋味都不是。 减去十岁,他高兴。作为一名搞科研的专业干部。他知道时间的珍贵。特别是对他这样一个年近半百的中年知识分子,能追回十年光阴,真是天赐良机。看看国外的资料:二十多岁取得科研成果,在国际会议上一纸论文倾倒全球,三十多岁在某个领域里遥遥领先,被公认是国际权威人士,这样的先例比比皆是。再看看自己,大学里的学习尖子,导师眼里的俊才,基础不比别人差。只可惜生不逢时,被打发去修理地球。待重新捡起泛黄的技术资料,早巳觉得眼也生,脑也空,手也抖了,现在,突然补回十年时间,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了。倘若更加勤奋些,科研条件更好些,少为扯皮、跑腿耽误功夫,那么,他可以把十年时间变成二十年,可以在攀登世界科学技术高峰的征途上大显身手。 他高兴,同其他人一样高兴,甚至比其他人更高兴。 可是,他的同事拍拍他的肩膀说: “老张,你高兴什么?” “怎么啦?”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不该高兴。 “减去十岁,季文耀今年五十四,他不会退了,你的局长也吹了。” 是啊,是啊,减去十岁,季文耀不会退,他也不愿意退,正好留在局长的位子上。自己呢? 当然就当不上局长,还是个工程师,还搞自己的科研项目,还钻在实验室和图书馆里……可是,前天部里刚把自己找去,说是老季过线了,这回要退下来,局里的工作决定让我…… 这,这还算不算数呢? 他确实不想当官。在他的履历表上,最高的职务是小组长,最高的政治阅历是召集过小组会。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的名字会同任何官衔连在一起,更不用说同“局长”这么高的官衔连在一起。他从小就是个“书呆子”。文化大革命中是个“走白专道路的修正主义苗子”。粉碎“四人帮”以后,更是一头扎进实验室,整天不跟人说一句话。 可是,七搞八搞,不知怎么搞的,选拔第三梯队的时候,把他选上了。几次调整班子搞民意测验,他都名列前茅,就像他上学读书时总考前三名一样。这一次,部里找去谈话,似乎已经铁板钉钉子了。就这样,他心里还是不明白: 自己曾经在什么场合,在什么事情上,表现出了领导才能,以致得到上级的垂青和群众的信戴。想来想去,他觉得十分惭愧。他从没有行政工作的才能,更何况领导才能? 他的妻子薛敏如是个貌不惊人、才不出众的贤妻良母。对丈夫的事情,乃至丈夫机关里的是非纷争,都能洞若观火。薛敏如说: “正因为你缺乏领导才能,所以才把你选到领导岗位上。” 张明明始而愕然:这是什么怪话?继而一想:似乎也有点道理。或许正因为自己缺乏领导才能,没有主见,不参与高位的逐鹿,也容易使各方面放心,结果就得到了这样的机遇。 当然,“反对派”也是有的。据说有一次局党组开会,为了张明明的“问题”争了一下午。争的什么,他不清楚。自己有什么“问题”,他也不清楚。只觉得从此之后他就变成了一个“有争议的人”。而这个“争议”,只有到他出任局长那一天才算统一了,他的“问题”才算澄清了。 就在这种不断的民意测验和不断的争议中,张明明渐渐地习惯了自己的角色,习惯了被人们看作是即将“高升”的人,也习惯了被人们认为是“有争议的人”。甚至有时还朦朦胧胧地觉得,或许自己真的是可以当好这个局长的,尽管自己从来没有当过。 “当就当吧,”敏如说,“反正也不是你自己争的。当上局长,起码上下班不用挤公共汽车了。” 可是,现在又当不成了。遗憾吗? 有一点,也不全是。还是那句话:不知什么滋味。 带着这种茫然之感。张明明回到家里。 “回来了? 正好,菜刚炒好。”薛敏如转身走进厨房,端出一荤一素一碗榨菜鸡蛋汤,荤的不腻,素的碧绿,十分诱人。 妻子是治家能手,温柔体贴,心灵手巧。三年困难时期,东邻西舍,不是肝炎,就是浮肿。薛敏如粗粮细作,肉骨头熬汤,西瓜皮做菜,保得了一家安康。如今农贸市场开放,鱼肉提价,谁家不说“吃不起”。敏如自有一套“花钱不多,吃得不错”的采购方法和烹调绝技。看到这可口的饭菜,张明明洗了手,坐到桌边,立刻拿起筷子来。 “芹菜很嫩。”张明明说,“价钱不贵吧?报上说,多吃芹菜降血压。” 薛敏如笑而不答。 “榨菜也是好东西,汤里搁上一点,鲜极了。” 薛敏如仍是笑而不答。 “笋干菜烧肉……”张明明还在赞美这顿家常晚饭,好像他是一名美食家。 薛敏如笑了笑,打断他的话问道: “你今天是怎么啦? 出了什么事?” “没有啊,什么事也没有哇!”张明明做出很吃惊的样子,“我正在说你的菜做得好……” “你天天吃,从来不说好坏,今天是怎么啦?”薛敏如还是笑着。 张明明有点招架不住了。 “从来不说,所以今天要说……” “得了吧,你心里有事瞒着我。”聪明的妻子一语道破。 张明明叹了口气,把筷子放下了: “不是有事瞒你,是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不知怎么告诉你才好。” 薛敏如得意地笑了,别瞧丈夫是个搞科研的专业干部,他的专业知识高深莫测,但在察言观色这一行中,在心理分析这一门里,他永远是自己手下的败将。 “不要紧,你说说看。”薛敏如像一个耐心的老师鼓励学生似的。 “今天有一个消息:马上要公布一个文件,人人减去十岁。” “不可能。” “真的。” “真的?” “真的。” 薛敏如想了想,水汪汪的大眼睛望着他,笑道: “你的局长当不上了。” “当不上了。” “心里不好受?” “不是不好受。我也说不清楚,反正不是滋味。” 张明明拿起筷子,扒拉着碗里的米粒儿,又说: “本来,我就不是当官的料,我也不想当这个官。可是,这几年叫他们闹腾的,好像这个局长的位置就该我来坐了。可,现在忽然又变了,心里总有那么点……” 他找不到恰当的词儿。 薛敏如干干脆脆地说: “不当就不当。不当才好呢。你以为局长是好当的?” 张明明抬起头来望着妻子。她决断之果敢,语气之坚决,使他吃惊。前些日子,当他告诉她,自己马上要当局长时,她也曾高兴过一阵,而且是由衷地高兴。她说过,“你看你,也没争,也没抢,局长的桂冠就加在你头上了。”现在,桂冠落地,她一不心疼,二不气恼,好像从来没有这回事。 “局长,局长,一局之长,事无巨细,都找到你头上来,你受得了吗?”她又说,“分房子,评职称,发奖金,人事纠纷,财务账目,子女就业,孩子入托,都要你管,你管得了吗?” 是啊,谁管得了这么多! “你还是搞你的专业吧! 补给你十年时间,你在专业上的成就就大不一样了……” 是啊,是啊,那真大不一样了。 张明明觉得气顺了,心里平静了。一种轻柔、温馨、美好的感情油然而生。 这一晚上床睡觉时,他觉得会睡得很好。可是,半夜时他还是醒了,心里仍然有一点遗憾,有一种失落的感觉。 三十九岁的郑镇海骑车一口气冲出大楼回到家,把那件旧灰褂子一脱摔在了椅子上。他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这一减十岁,似乎有许多重要的事需要立即动手去干。 “喂!”他喊了一声,屋子里竟没人答应。十岁的儿子照例在胡同里疯玩儿,老婆呢,也没像平日那么应一声,她哪儿去啦?串门去啦? 哼! 这还象个家吗? 自己制作的小沙发比例不对头。人坐上去背脊够不着椅背,扶手低,坐垫高,胳膊搁上去别说不舒服,还怪累得慌。都是她看人家有了沙发眼馋,没钱买死活要自个儿做。小家子气!其实,家家都摆这么一套沙发,像干部服似的,别提多闷气了。小市民! 是啊,当时怎么就找了她! 瞧她那一家人吧,除了吃喝穿戴、工资外快,不谈别的,庸俗透顶。家教最重要。她简直跟她妈一个模子刻的,说起话来粗声粗气,生一个孩子就胖得像个桶,要长相没长相,要身材没身材,要性格没性格。唉,当初怎么就找了她! 嗐! 都是那会儿瞎着急,眼瞅着已近而立之年,还是光棍一条,饥不择食。这回,这回减去十岁,才二十九! 那可得认真考虑考虑这问题。昨天就为买了条好烟,她又喊又跳的,还威胁日子没法过了,要离婚。离婚?!离就离! 二十九的男青年,找对象最合适的年龄,还怕找不着个水葱儿似的大姑娘,二十二、三刚毕业的大学生,文文雅雅的,又现代派。大学生配大学生,她才是个中专的半瓶子! 真是悔不该当初! 是要重新安排一下生活。不能这么窝窝囊囊的将就下去了。这人,她上哪儿去了呢? 这人,下了班,冲出大楼,就直奔了妇女服装商店。 减去十岁,振奋得月娟心花怒放,想入非非。一个差一岁就四十的女人,忽然折回去成了二十九岁的年轻女郎,这对她,真是喜从天降,是用世上一切值钱的东西都无法衡量的宝物啊! 二十九岁,多年轻! 多光明! 她低头一看自己那一身毫无色彩、毫无魅力、死气沉沉的服装,禁不住一阵彻骨的伤心愤恨。她一口气跑进商店,噔、噔、噔直奔时装展销专柜,两眼扫描器似地在悬挂着的一件件耀眼的连衣裙上扫过。突然,一件大红镶白纱皱边的连衣裙击中了她。她请女售货员拿来试一试。青春年少的女售货员上下打量了她一眼,脸上没有一丝柔和的情状,整个脸儿像冰冷的石头雕出来的。这冰冷的后边就是无言的轻蔑。 怎么?难道我不配穿这个? 月娟心里憋着一股气,就像她近几年去买衣服时常有的心情一样:好不容易相中了一件,镇海总规劝她:“你穿这样的不合适,显得太年轻了。”太年轻了有什么不好? 像个老太婆才好?! 常常是衣服没买成,生一肚子气,回家还得斗一宿嘴。遇上他这号的保守派算是倒一辈子霉! 别跟这售货员一般见识,买东西,我给钱,你拿货,管你屁了! 小妞儿懂什么,她知道就要发文件了吗? 二十九的人怎么不能穿这个? 中国人就是保守,人家国外的老太太越老越俏,八十岁还穿红着绿的呢。衣服穿我自己身上,碍你的事啦?你死眉瞪眼,我也得买! 给了钱,月娟当时就进试衣室穿上了。她照了照那窄条的镜子,发胖的身子紧箍在大红的连衣裙里,火红的一片,显得面积大了些,但非常热烈够劲儿。唉,没有办法,慢慢减肥吧。年龄可以减去十岁,上级一个文件就解决了。体重减去十斤,那可得自己下苦功夫。动物脂肪早已戒绝,淀粉食品也降到最低限度,连水果都不敢多吃,还怎么减肥呢? 她呼哧呼哧地回到家,推开门,像一团火似地窜进了屋,吓得郑镇海倏地从沙发上跳起来: “你这是怎么啦?” “什么怎么啦?” “哪儿,哪儿去弄了这么身衣服”? “买的。怎么样?”月娟拎起连衣裙的下摆,做了一个时装模特儿的转身动作,脸上露出不可抑制的媚笑。 郑镇海兜头一盆冰水泼来: “别以为红的绿的就好看,分穿在什么人身上。” “穿在我身上怎么啦?” “穿这个,这,合适吗? 是穿这种裙子的年纪吗? 你想想自己多大岁数了?” “我想了,想好了才买的。二十九! 二十九正是打扮的年纪。” “二十九?”郑镇海一时又懵了。 “不错,二十九。减去十岁,二十九,还差一个月呢。我偏要穿红,我偏要穿绿!”月娟手舞足蹈,俨然像一名流行歌星,在舞台上扭扭捏捏半痴半傻地跑来跑去。 她,她,她这么大岁数,这么粗的腰,她,她减去十岁就这样儿,叫人目不忍睹。郑镇海闭了闭眼,猛地睁开,瞪着她说: “上级发文件减去十岁,是为了更好地调动干部的青春活力,更好地干四化,不是为了穿衣打扮!” “穿衣打扮碍着四化啦?”月娟跳了起来,“哪份文件说不准穿衣打扮了? 你说!” “我是说,打扮也得看看自己的实际情况,自己的身材……” “我身材怎么了?”一语戳到痛处,月娟不依不饶了,“实话告诉你。你嫌我胖,我还嫌你瘦呢,瞧你瘦得小鸡子似的,头上的皱纹像电车道,走三步路就喘、咳,当初我图什么,不就图个知识分子吗! 跟着你,啥政策也落实不到头上,就担了个知识分子的虚名儿,要穿没穿的,要住没住的。怎么着?如今我二十九,早着呢,到大街上随便找个个体户,管他卖糖葫芦卖花生米,哪个不比你强?” “你,你有本事找去!” “简单得很,今儿离了明儿我就找人登记去!” “离,离就离!” 这句话可捅了大漏子。平常日子,“离婚”二字,是月娟的专用名词,三天两头挂在嘴上,郑镇海从不敢借用。今天这死鬼吃了豹子胆,居然敢提离婚,这还了得? 全是这破研究会闹腾的! 月娟气鼓鼓地一头朝郑镇海撞去,嘴里骂道: “减了十岁,你骨头就轻了,就你那样儿想离婚,门儿也没有。” “减了十岁,你以为世界就属于你了,妄想!” “小林,明天文化宫有舞会,这儿有你一张票。”工会的李大姐冲林素芬招手。林素芬理也没理,三步并作两步,冲出了机关大楼。 减去十岁,林素芬才十九。摘去了“大女”的帽子。一个含苞待放的少女,还用得着工会操心?还用得着婚姻介绍所的帮忙? 还用得着到组织的舞会上去找伴? 统统一边去吧! 二十九岁的老姑娘,走到哪儿,哪儿都投来叫人难以忍受的目光:怜悯、讥讽、戒备、怀疑……怜她茕茕孑立,形影相吊;讥她眼界过高,自误终身;戒她神经过敏,触景伤情;疑她歇斯底里,性格变态。一天中午,她在开水炉前冲了一碗方便面,还卧了两个鸡子儿,就听得背后有人说话: “还挺会自我保养呢!” “心理变态。” 她的眼泪直往心里流。难道,二十九岁的姑娘中午不去食堂,自己卧两个鸡蛋就是心理变态?这是哪本心理学上的论点? 就连挚友的关怀,三句话也离不开“找个对象一块儿过吧”。好像二十九岁还没嫁人就犯了弥天大罪,就成了众矢之的,就该让人家当成谈话资料。茶余饭后,颠来倒去,在众人的舌头上滚来滚去,使你灵魂不得安宁。人生在世,难道除了快嫁人,快找男人一块儿过,就再也没有更重要、更迫切的事情了? 可悲、可恨、可恼、可笑! 这一下,解放了。姑娘今年一十九,你们统统闭上嘴吧! 仰头望着晴朗的蓝天,那朵朵白云仿佛变成了条条的小手绢,顷刻间堵上了一切好事者的嘴。多痛快呀! 小林昂首挺胸。目不侧视,步履轻快,一阵风似地扑向存车棚,推着她那辆“飞鸽”,自己也像只自由的鸽子似的飞出了大门。 下班时间,行人如潮。国营商店、大集体、个体户小铺,一家挨着一家。流行歌曲,此起彼伏。“我爱你……” “你不爱我……” “我的生活不能没有你……” “你心中根本没有我……” 什么词儿? 统统见鬼去吧! 爱情,不再是急待脱手的陈货。十九岁,有的是时间,有的是机会。当务之急是学习,充实自己,提高自己。有了真才实学,能够有益于社会,能够造福于人民,才会得到社会的尊重,才活得充实,过得有意义。到那时,爱情自己来到身边,她当然不会拒绝。但那该是一种悄悄的爱,朦胧的爱,深沉的爱。 考大学,一定要考上大学。十九岁,正是上大学的年纪,再也不能荒废了。电大夜大,弄得好,可以混张文凭。可毕竟不是正规大学,哪能赶上北大清华?这一辈子,毁就毁在学业荒废上。严格说来,只是初小程度,小学四年级就赶上了那场“革命”,在胡同里跳了几年猴皮筋就高小毕业了。上了中学,坐在教室里如坐飞机,老师教的十之八九不明白,晕晕乎乎,糊里糊涂照样毕了业。插队落户,劳动锻炼,学的一点点知识也还给老师了。“革命”完毕,回城待业,没着没落。好不容易进了局里的劳动服务公司,还是个大集体。这本账如此算来,好像生活中剩下的,就只有一件事了—找个对象成家,生孩子,洗尿片,油盐酱醋,买粮食,换煤气,吵架斗嘴,了此一生。 一生就这么交代了?林素芬不甘心。不服气。来到这世界,总得干一点什么,留下一点什么,然而,初小的程度,不种粮食不挖煤,工人农民算不上,知识分子没知识,在人群中如孤魂野鬼。 从A、B、C学起。她几乎把业余时间全用在五花八门的补习班里,把工资的一大半用在交学费买教材了。语文、数学、英语、绘画,样样补,样样习。补来补去,这样的补太慢了,太吃力了。她想速成。年龄威胁着她。再不速成,就算是千里马,牵到伯乐跟前也老了,还能被相中? 她专修英语,想来一个突破。《九百句》、《新概念》、广播教材、电视课程、补习学校,齐头并进。过了一个月,她才发现这个突破口前拥挤着多少个爆破手啊! 都是她这样的大男大女,都想抄近路登龙门。而这并不是一条捷径。就算英文学得不错,中国文化水平很低,能派什么用场? 英译中,中译英? 外语学院毕业成材的多的是! 人家不指望在你待业青年里发现苗子! 她又转向“文学创作函授大学”。走文学之路,写点小说,写点诗歌,把我们一代青年的苦闷徬徨,向往追求,倾泻纸上。让广大读者,让二十一世纪青年,知道在这世界上,在历史的一瞬间,曾经有过被历史愚弄的不公平的一代。他们是无辜的,他们失去了本该属于他们的一切,得到的却是不应由他们承受的沉重的负担。他们将背负着这沉重的包袱,走向人生的尽头。 然而,文学道路,谈何容易?看那些同龄人的作品,不能入目,自己拿起笔来,不知从何下手。稿纸撕去几大本,家里人惶恐不安,以为着了魔。看来,并不是人人都能当作家的。 或许,还是去学会计? 现在,会计人才奇缺…… 三心二意,举棋不定。彷徨、苦闷、自己不认识自己,不知道想干什么,不知道该干什么。有人说:“别瞎想了,到了这个年纪,混吧。”有人说:“结了婚,就踏实了。” 而这,都是她最不愿意的…… 现在,地覆天翻,花香鸟语,世界突然之间变得无限美好,减去十岁,我才十九,什么彷徨,什么苦闷,什么伤心失意,见鬼去吧! 生活没有抛弃我,世界重新属于我。我将珍惜未来的每一寸光阴,决不虚度。我将确定生活的每一个座标,决不转向。我要读书,我要上学,要有真才实学。这是第一站的目标。 对,从今天开始,从现在开始,向着这目标前进。 她骑上车,满脸微笑,直奔新华书店教科书门市部。 次日清晨,机关里热气腾腾。楼上楼下,楼里楼外,熙熙攘攘,欢声笑语,不绝于耳。患心脏病的人说上楼就上楼,噌噌地一口气上了五楼,气不喘,心不跳,面不变色,跟没病的人一样。六十多岁的人,平日言慢语迟、声低气衰的老同志,嗓门一下子变高了,说出话来当当的,走廊这头就听得见他在那头嚷嚷。 各个办公室的门都大开着,人们赶集似地串来串去,亲切地倾吐着自己的激动、快慰、理想和无穷无尽的计划。 忽然有人倡议: “走,上街,游行,庆祝又一次解放!” 一呼百应,人们立即行动起来。有制横幅标语的,有做红绿小旗的。文体委员从库房里抬出了圆桌面大的大鼓,抱出了扭秧歌的红绸子。一霎时,队伍在大楼前集合了。横幅标语上红底黄字:“欢庆青春归来”。各式小旗上倾吐了人们的肺腑之言:“拥护年龄研究会的英明决策”、“焕发青春,献身四化”、“青春万岁!” 激动人心的大鼓敲起来了。季文耀觉得浑身的血都在沸腾。他高站在台阶上,正想说几句助威的话,亲自领导这次的盛大游行,忽然看见几十名已经办了离职手续的老同志冲了进来,直奔他眼前问道: “减去十岁,为什么不通知我们?” “你们……已经离了……”季文耀说。 “不行! 那不行!”老人们齐声嚷起来。 季文耀双手高举,在台阶上大喊道: “同志们,不要嚷,不………” 人们哪里肯听,人声如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响彻云霄: “减去十岁,机会均等,人人有份,干吗把我们撇下不管?” “我们要按文件办事了,不能随心所欲。”季文耀的声音提到高八度。 “文件在哪儿,为什么不传达?” “拿文件给我们看!” “为什么不给看文件?” 季文耀扭头问办公室主任: “文件呢?” 办公室主任愣头嚓脑地回答: “我不知道哇!” 正僵持中,一批新招进来的十八、九岁的青工嚷起来:“减去十岁,我们不干。” “十八年饭白吃了,有了工作,又把我们打发回去上小学三年级,没门儿!” 机关幼儿园的娃娃们,也像一群小鸭子似地扑到季文耀跟前,抱着腿,拽着手叽叽喳喳叫道:“减十岁,我们回哪呀?” “我妈好不容易生下我,还开了肚子呢!” 季文耀应接不暇,又大叫办公室主任:“文件,文件,快把文件找来。” 办公室主任手足无措,季文耀训斥道:“还不快到机要室去找!” 办公室主任赶忙跑到机要室,翻遍了文件夹,没有。 热心人马上提供线索: “会不会存进档案室了?” “会不会哪个处借去了?” “糟糕!要是扔到废纸篓就完了!” 在一片纷乱中,季文耀反而冷静下来,马上布置任务: “找,发动群众,大家动手一齐找,要细细的找,不要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队伍要解散吗?”办公室主任请示。 “为什么要解散?先找文件!” |





今天是愚人节,再读她的这篇带有“愚人节”风味的小说,趣味横生,一条查不出源头的小道消息,像一阵风,把那些中年人、中老年人、老年人,还有青年人,裹在外面遮丑的各色新衣都撕扯了下来,露出了平日里说不出口却在心里横竖琢磨的众生相。
我们在作者妙梦的描述中,看到了一幅幅焦灼的人心世态图,那腌臜的私欲和秘密都交织在一起,在这阵不明源头的风的劲吹下,曝了光。各色人等都在这股春风的吹拂下,开始了做梦...
谌容的蓝色幽默,使人在笑过以后,沉入人性的思考。
当然了,文件呢?--找不到了,可队伍不解散,这梦呀,还要继续做下去啊... 就像附歌里唱的:-- 谁在风里唱,花落好心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