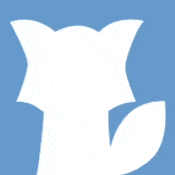一人两狗在路上。讲述者供图
一人两狗在路上。讲述者供图
摘要:
今年一月,流浪博主阿星四年来第一次回到家。再过几年,阿星就四十岁了,他没有结婚,没有工作,一个人和两只狗,骑着三轮车流浪了四年。B站上关注他的粉丝有20多万,都说在他的视频里看到了逃离996,远离物欲和社会竞争的自由。弹幕里到处飘着,“好羡慕”,“他做了自己想做但不敢做的事”。
四年前的那场出走,对阿星来说其实是一次别无选择的逃离。他从小被认为智力低下,直至成年都自卑怯懦,失业多年,在现实生活中提不起力气,将自己视为“废物”。他去过深圳三和,看到人们扎堆睡在广场上,争抢充满尿味的沙发,待不下去又回到家里,把自己关起来。
2018年2月,他决定再次出走,以摆摊为生,从广东佛山北上新疆,重新闯入曾令他恐惧的房门外的世界——被金钱、人际交往还有家庭责任构筑的世界。了解阿星的故事后,会发现都市人对“流浪”的想象,需要摘掉外层滤镜才能抵达沉重的现实。
文/张雅丽
编辑/陶若谷
房间
午夜,广东佛山一幢老式居民楼的楼道里,阿星低声重复,“很紧张,很紧张。”再往上一层,就是他自己的家。楼道里的灯坏了,四下黑洞洞的。他压低声音,生怕被父母发现。2022年元旦,因为办理证件,阿星回到广东,下飞机的时候已经凌晨,他在街上又晃了很久才往家走。离家流浪四年,这是他第一次回家。
“不知道会不会吓到父母。”他面对手机镜头说,把这个重要的时刻录在视频VLOG里。与离家时相比,阿星看上去更像一个流浪者——长发及肩,扎起来,胡子垂到下巴,瘦得不过百斤。“其实我现在过得也不错。”坐在楼道里,他给自己打气。
他从小到大都叫阿星,“星”是真名里的一个字,如果推算的话,今年起码37岁了。他不喜欢别人询问他的年龄,躲避的方式是回答对方,“你猜”。在这次流浪之前,阿星的活动范围就是家里一间狭小的屋子,生活完全蛰伏在里面。大学毕业后,他失业好多年,每天的生活大概只有三件事:吃饭、睡觉、上网。
泡在网上的时间起码12小时,没日没夜。饿了就让母亲把饭端来,在屋里吃。游戏打累了就睡觉,醒来继续打。“明天我一定去找工作。” 但第二天拾不起力气,拖着一天又过去。一连许多天,他可以不跟现实中的人说一句话。
“妈咪,爸爸。”四年后,阿星终于鼓起勇气上楼,在门口喊。父亲开的门,他头发白了,胖了一些,母亲的牙齿快掉光了。新装的空调和家具也提醒阿星,自己走了不短的时间。
 流浪路上,某纪录片团队为阿星拍的照片。讲述者供图
流浪路上,某纪录片团队为阿星拍的照片。讲述者供图
此前的三十多年中,阿星一直游离在人群边缘。他一共做过五份工作,但每一份都做不过几个月。第一次因为手脚太慢,后来的理由都差不多——跟同事和老板都相处不来,他尝试跟同事们开启话题,两三次后发现,各说各话。
阿星逃回到家里,关上房门,最长可以半个月不出家门。即使是出去,也只敢在晚上。夜晚安静,街坊领居都回家了,不会对他投来意味不明的目光。很长时间,他没有固定的收入,靠父母的退休金度日。
“废物。”房门外,父亲这样骂他。这话他早就听习惯了,心里没什么波澜,甚至自己都认同。街坊们都知道,阿星曾是个“弱智仔”。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他因为调皮被老师选中去做试卷——阿星觉得题目很奇怪,“叶子”的反义词是什么?他答不上来,最终这张试卷宣告了他智力低下。
在这个当年只吃得起鱼骨的家庭,阿星有一个无缘无故就会打人的父亲,一个内向软弱的母亲。全家埋头吃饭的时候,父亲会突然狠狠地用筷子敲打母亲的头,因为觉得炒豆角里盐放得太多。“我弟的性格像我妈一样软弱。”姐姐志玉说。饭桌上,父亲夸奖亲戚家的小孩成绩好,志玉听了烦,摔了碗筷就走。阿星一声不吭,只吃饭。
贴上“弱智仔”的标签后,他成了同学中一个异类。阿星现在还记得,老师对全班同学说,“连阿星都能做对的题,你们不能不会做。”没有人再跟他一起玩,他讨厌所有集体活动,因为总是一个人。同学有时把他逼到墙角,让他跪下磕头,索要零花钱。
志玉也回忆起一种模糊的羞耻感,当年结伴上下学的时候她曾对弟弟说,“离我远点,别跟别人说你是我弟。” 阿星垂着头,远远地跟着回家。
在志玉的印象里,弟弟从小到大只交过一个朋友。为了融入别人,阿星讲话时习惯放低声音和姿态。他偷偷跟在同学身后,研习他们如何说话。亲戚家生孩子,大冬天他主动帮人家看羊,渴望被人群接纳。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进入社会。
年过三十后,作为家里唯一一个儿子,阿星清楚要养家的责任,但父亲生病住院,却拿不出治病的钱。坐在医院的长凳上,他看看自己,细瘦羸弱的肩膀,拿什么养呢?这念头让他在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可第二天早晨起来,继续一头扎进网游里。
2018年2月24日,阿星决定从那个封闭的房间出来,全国各地,总能找一个自己落脚的地方。
出发那天,他蹬着六百块收来的蓝色三轮车,车斗里堆着帐篷、厨具等装备,带着两条狗,留下在门口挽留的母亲,独自上路。他跟母亲说,自己去隔壁城市做小生意。
四千公里外的新疆才是阿星真正的目的地,骑车去,归期不明。他特意选了日期带“四”的日子出发,心想,都这么不吉利了,如果有什么不测,大概是我的命,认了。选择新疆的原因也十分简单——足够远。
 阿星刚出发的时候。讲述者供图
阿星刚出发的时候。讲述者供图
很多第一次
见到阿星时,全职妈妈辛悦的直觉是,“如果是另一个人,可能会觉得他是个乞丐。” 但阿星说话慢吞吞的,嗓音细软、认真地回答了她所有问题。他的两只狗很调皮,不像其他流浪狗那样战战兢兢,凭这一点,辛悦下了判断,这个人一定对狗很好。
在社交平台上,她一直在关注阿星的世界——一个人和两只狗的骑行流浪。阿星会分享遇到了谁,又救了哪只狗,旅居在凉山彝族老乡家,老乡从房梁上拿下来腊肉招待他。那感觉就像自己走了一段路一样,辛悦说。她从小喜欢狗,养了许多只,因为不舍得寄养,放弃了出门远行,家里还开了宠物医院。
辛悦大学读的是野生动物保护,曾期盼去可可西里工作。婚后她厌倦了与领导相处,全身心投入家庭,成了孩子的陪读妈妈,向往自由却被生活拴住。
两年前阿星流浪到辛悦所在的城市,四川西昌,辛悦决定见见他,后来迫不及待地把他介绍给了自己的朋友们——有宠物店老板,也有体制内工作者,身份各异。辛悦觉得身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替我们很多人走了一段没办法走的,心里的路。”
出来流浪后,阿星骑着三轮车一路往西北走,用手机记录他的生活,发在网上。很多人跟帖、追更,有像他一样失意的不愿上班的男孩,也有家中生变故的女士,给阿星留言,“即将开庭了,想去看看楼主和狗狗接触下正能量。”
 在3600米的高原休息。讲述者供图
在3600米的高原休息。讲述者供图
和多数人所想并不一样,路上并不是某种惬意和抒情的逃离。阿星出发时身上只有1500块,每天绕在脑子里的是今天吃什么、住哪里。
到达一个城镇,他会到市场里去,买几块钱的肉、便宜菜和摊主不要的内脏来煮。运气好的话,帐篷外会有好心人留下食物。没有吃食的时候,他会到饭店里去,跟老板讨要一些剩饭菜,说自己用来喂小狗。实际上,这些饭菜主要是他吃,“自己也要脸面。”
为了赚路费,他会在当地进一些货,摆在地上卖几天。手机配件、运动挎包、小玩具之类的都卖过,但时常入不敷出。
刚骑出去没多久,阿星就想回头,但车轮最终没有停下,“我已经没有别的选择。”阿星想,这是他突破原来世界的唯一一条狭小的路。出发前,他把微信里的联系人全都删除了,“原本我也没什么朋友。”
因为看了他的帖子,单亲女孩小敏一家专程去阳朔看望他。相处一周,临近分别,小敏领着阿星东转西看,就不说分开。“她舍不得我”,阿星忽然发现,自己获得了一些过去难以获得的东西。不久后有人留言:“楼主,你封神了,恭喜啊!”还截图给他看。阿星回复:“谢谢你。”在此之前,他的人生里,诸如此类的肯定屈指可数。
流浪到桂林,阿星第一次收到了女孩送的东西。“是一个穿白裙子的女孩,给我送食物。”他以前很少收到过礼物,包括过生日,后来,索性鄙视过生日这件事。女孩送来吃的,阿星不敢猜测对方的心思,“她太美好了。” 犹豫了好些天,也没开口留下对方的联系方式。
还有一天,阿星记得清楚,他赶了很久的路,精疲力尽,两只小狗却上蹿下跳,极力挣脱绳子。多次呵止不奏效,阿星狠狠地打了它们一顿,“我太累了”。
在这一瞬间他突然想到了父亲,一个困窘的煤厂工人,“他应该也有他的压力吧。” 在此之前,阿星无法理解为什么父亲的巴掌会毫无征兆地落下来。只因为下雨忘记带伞,回到家就被父亲按在地上打。母亲从来不敢还手,从某一天开始对着空气自言自语,“有人骂我。”她说,她要骂回去。在阿星的记忆中,一切都源于父亲的拳头。
“面对无解的生活压力时,或许暴力是他最为高效的解决方式。”阿星第一次这么想,他开始回忆父亲生病那天,他赶到医院,父亲见到他说,“赶紧滚”,但紧接着又说,“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万一有什么病传染给你”。流浪的路上,阿星开始思考,也许父亲只是不会表达?
在大理的某一天,阿星坐在自己的摊位前面,望着人群,他想起好久没给父母打电话了。拨通了家里的座机号码,发现停机了。“他们不要我了。”阿星想。他把手机和难过一起收起来。
 穿越无人区。讲述者供图
穿越无人区。讲述者供图
在逃“大神”
在「流浪吧」的789万条帖子中,小梁发现了阿星,看他的视频解压。一次工作面试,候场时,她紧张极了。翻看手机,发现阿星的视频更新了——他走在青得望不到边的草原上,身边环绕着两只欢脱的小狗。“世界这么美好,即便没通过又怎么样呢?”小梁当即就想。
四五年前小梁还是个大学生,因为学了不感兴趣的经济专业整日烦闷。她是教师子女,父母对她的控制一直持续到大学选专业,要求她只能考第一或者一百分。读大学之前,小梁几乎没有一个人出过门,连参加同学聚会都要被开车接送到门口。
“我不想这样活了,没意思。”她在网上闲逛,发现了「流浪吧」。阿星让小梁看到了另一种生活。最初,怀着见证一个底层之人能否成功的心态关注阿星,但一看就是四年。“他治愈了我们。”在阿星的粉丝群里,大家都这样说。
粉丝群里人不多,但对阿星来说这样的关注已经足够多了。互联网重构了阿星的生活。四年间,他走在路上,从来没有离开过网络。出发之前,阿星就有过几次短暂的“出逃”。2015年,他第一次动了流浪的念头,身边的人说不切实际,但贴吧里的人都鼓励他。
吧友们互称“浪吧老哥”,在这里更新各地的房租价格、哪里可以领到免费斋饭。他去过西藏、海南的一些地方,最穷的时候,就睡在路边。但在网上他为自己修筑了一个小小的屋子,试图在这里找到自己的存在,栖身于此。
三和大神最火的那些年,这里到处都在讨论“挂逼”(很丧,彻底废了)、“躺尸”、“日结”。里面聚集了很多在现实生活中提不起力气的人,终日在喊:“坚决不上(班)!打死都不上!没劲!讨厌任何人!” 阿星时常出现在吧里,“看到他们,才能找到自信。”
为了能在这次流浪前见一面嫁到香港的姐姐,阿星去了深圳,结果刚到行李就被偷了,游荡在深圳街头,身无分文的时候就睡在医院急诊室。吧里的人劝他,“来总部(三和)当大神。”
他真的去过,看到人们扎堆睡在广场上,争抢充满尿味的沙发。一个胖子像滩烂泥一样四仰八叉地睡在道上,苍蝇在他身上乱飞,阿星看见他的时候,他永远在睡。“他还活着吗?”阿星想。
 阿星在路上。讲述者供图
阿星在路上。讲述者供图
待了一个星期,阿星离开了三和,后来彻底离开了深圳,在这座都市里,他给年轻女孩带过路,走到一半,女孩在身后悄悄地溜走了。看到中年女性费力提行李,他上前帮忙,对方以为他要抢劫,逃走了。“穷是原罪。”阿星说,如果我穿着体面,还会这样吗?他想到更远的地方看看,试试像他这样的人,不偷不抢不骗,究竟能不能活下来。
2018年夏秋在大理,阿星曾有过念头,如果留下来,或许也不错。这里聚集着来自各地的人——常年住帐篷的老头,自创一派的少女,整日习武的武林高手……阿星觉得,自己不再像过去一样显得怪异和特殊。大家一起在街边吆喝摆摊,到寺庙里吃便宜管饱的斋饭。刚到的第一个月,他住在800块的出租屋里。但很快,第二个月就没有钱再付房租。他又住回帐篷,但起码不再用为吃饭发愁。
同伴粉条和阿星同一天到大理。粉条脸上有白癜风,在过去的生活里也不受欢迎,阿星觉得找到了同类,交上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朋友。阿星一度以为,大理就是自己的“乌托邦”了。
但他发现好像并没有脱离与人之间的竞争。他记得一个女生受伤了,大家蜂拥上去帮她包扎,他不擅长热络的表达,手也笨,只能站在人群外面,显得手足无措。“原来连帮助人都存在竞争。” 他想,“我实在太没用了。”
这种失落还表现在最引起自卑心理的人,不是过去自己所认为的富豪精英,而是朋友粉条——他身形高大,开朗善谈,每次集体活动,他几乎都身处在人群中央,人们都爱听他的。“我的价值是什么呢?”阿星决定离开大理,继续上路。
2019年,阿星途经云南、四川,越走越远。在流浪吧,他已经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大神”。阿星遇到了阿成——一个自称是他粉丝的人,提出合伙运营短视频账号。但很快,一种所熟悉的,被支配的感觉再次出现。阿星拍回来的视频,阿成看了总觉得不满意。阿星甚至不知道视频账号的密码,视频拍了小半年,最终他只拿到2000多块。
“那时候的我,连恨都不敢恨。” 回想起来,阿星说。他曾有过念头,作为合伙人,连账号密码都不知道,这看上去不太妥当。但很快他自我否定了,他不敢跟对方提出要求。最终,阿星提出散伙。
但这一次分离,他觉察出内心的欣喜,“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活了。”阿星开始独立制作短视频,成了几十万粉丝的流浪博主“乐浪星”——小狗乐乐和浪浪,还有他。
 在戈壁滩,喂两只小狗吃饭。讲述者供图
在戈壁滩,喂两只小狗吃饭。讲述者供图
栖身之所
成为“乐浪星”后,阿星打算把社交账号当作一间属于他的新屋子,起码在2020年8月之前,他这样想。那时粉丝数已经涨到十多万,但随后其他声音也多起来。
因为被黑房东赶出门,阿星带着两只狗又住了一段时间帐篷。有人刷出弹幕,“你都这么大(号)的博主了还住帐篷,卖惨!” “你这是虐待狗狗!”
更激烈的还在后面。去年1月,和阿星很久没联系的辛悦突然收到他打来的视频。“我该怎么办?”视频里,头发散乱的阿星抱着乐乐大哭,小狗看上去是中毒了。三年前,阿星第一次见到乐乐时,它正在被大狗追,阿星把它捡回了家。乐乐跟着他一路从广东老家流浪到甘肃,路上因为误食烈性老鼠药,死了。
90多万人看到了他抱着乐乐大哭的视频,咒骂从3000多条弹幕涌进来,“乐乐的死都怪你!” “狗都死了还有心情拍视频!”还有人质疑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摆拍。
不想走了。流浪三年,因为乐乐的死,阿星第一次有了这个念头。他说那时不敢看评论,过去的回忆都冒出来了——被同学堵在墙角一样,对方让他下跪,他顺从地跪下去;偷钱去游戏厅,被父亲打……他打开手机,搜索“自杀”,发现跳出来的页面都是劝阻的话。他想了想,不敢,还是算了。一切仿佛又回到了出发前那个昏暗的房间。
 流浪路上,阿星用狗粮、火腿、鸡胸肉给两只狗准备的食物。讲述者供图
流浪路上,阿星用狗粮、火腿、鸡胸肉给两只狗准备的食物。讲述者供图
在几年前的视频日志里,阿星说过,狗给了他纯粹的情感和快乐。还没出广东的时候,他推着三轮车翻一座巨大的山,累得精疲力竭。乐乐坐在车筐里,落了泪。
离开了大理的朋友,阿星在路上的同伴就是乐乐和浪浪。碰到有人挑衅,乐乐冲到阿星前面,仰起头狂吠,被对方一脚踢开。阿星和对方厮打起来。之前他很少跟人发生争执,因为不敢,姐姐志玉说,“佩服他,受了欺负从来不跟家里说。”
但那次为了乐乐,阿星打了一架——他想起在大理,和同伴闯进偷车贼窝,同伴往他身后躲,他往同伴身后躲,可两只狗为了保护自己,毫不犹豫地冲出来。
乐乐死后,阿星钻进出租屋待了一个月,把窗帘拉得严严实实,不再更新视频。饿到不行才吃一顿饭,剩下的时间就昏睡,浪浪跟着一起挨饿。
一直默默关注他的小梁在网上私信了阿星,用自己亲人过世的经历安慰他。她后来时常在困惑的时候找到阿星,在小梁眼里,阿星文笔好,人善良,在路上还救助其他流浪汉,“和那些大神不一样,他总在思考。” 最近,小梁不想再听父母的,想考自己喜欢的专业研究生。阿星对她说,“想做就去做吧,我这样的人都能流浪成功,你怕什么?”
出发前,阿星将流浪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自己的方式,克服困难,独立地生存。第二个阶段是重新融入社会,学会和人相处。阿星说,他能穿越无人区,雪山和戈壁,但一直以来难以穿越人心。他现在有了朋友,也有MCN公司想要跟他签约。“我最怕跟人签合同。”阿星说,一签合同,他觉得自己又失去了自己的意志和自由,又怕像新闻里的那些人一样,赔很多钱。
 在青海路边扎营。讲述者供图
在青海路边扎营。讲述者供图
第三阶段,阿星觉得应该有,但还没想好是什么。今年回家,父亲感觉儿子似乎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再跟家里要钱,在家里添家具和买药的时候,还会寄一些钱回来。他换掉了四年前让他“滚出去”的语气,用一种宽慰的语气对他说,“好男儿志在四方。”
父母不知道阿星在外流浪,姐姐志玉帮着一起骗他们,说阿星在外面做大生意。后来阿星得知,刚离开家的时候,父亲会到附近的公园和桥洞下面去找。姐姐也感觉到了阿星的变化,从某个时刻开始,志玉给他钱,他不需要了,也不再像过去那样没有主意。
有亲戚在网上发现了阿星。他们不敢相信这个曾经不工作、“不务正业”的人竟然靠着在外流浪,成了“大主播”。也有人说回来就别出去了,给你介绍个稳定工作,结婚生子吧。但阿星在家没待几天又走了,他对自己现在的状态颇为满意。在他看来,他不仅完成了独立生存的目标,有了相对可观的收入,更重要的是,“找到了自己的屋子。”
在很多个地方,阿星一直面临走还是留的选择。我的价值是什么?这个问题推他走了四年。起码在现在,阿星认为,那个栖身之所找到了——他承载了几十万人对自由流浪生活的关注,这很重要。
两个月前,阿星在敦煌的一个老旧小区落脚。他租了一间房,趁着春节去做了体检,希望能调养好身体,完成到达新疆的目标。
除夕那天,房东邀请他去吃火锅。过去的三十多年,阿星不喜欢过节,因为没有同学朋友邀请他,跟父母一起过,总觉得尴尬。这天,他来到房东家做客,并将这些拍成了视频发在网上。视频里他没带礼物,又被骂了。
 今年除夕夜,阿星和小狗看烟花。讲述者供图
今年除夕夜,阿星和小狗看烟花。讲述者供图
(文中志玉、辛悦、小梁为化名)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