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迷五色,心空四象
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
也当一回标题党,呵呵:)
其实,文怀沙的年龄,关我什么事?不过是当我看见朱季海的名字卷在这段公案中时,想起了一些往事。
现如今流行用“最后”作修饰语,比如“最后的贵族”、“最后一个太监”、“最后的母系氏族”、“最后一个莫西干人”、“最后一个女土司”、“最后一个地球公民”……还有“最后的沃氏三趾鹑”什么的。如果用“最后”去修饰朱季海,那他真就是姑苏城最后一位隐士了。所谓的“大隐隐朝市”,说的就是朱大隐士。
朱季海是颇有些林下之风的,虽不像竹林七贤那样宽袍广袖、飘逸如仙,但时出狂放之举,若在金庸的小说里,他就是“非汤武而薄周孔”的黄老邪,或者跟黄蓉没大没小的洪七公,反正有关他惊世骇俗的段子,着实在城里留下了一长串。你跟他在一起,千万不可遵辈份礼法,若尊称他“朱先生”、“朱大师”、“朱老”……,你就等着他瞧你不入流吧,反而是直呼“朱季海”、“老朱”的,他听着欢喜。可惜朱季海生错了时代,要是处在一个风流清逸的年头,不知该有多么肆意酣畅呢。
知道朱季海是因为他那本《楚辞解故》(中华书局,1963年12月第1版)。当时我不知中了什么邪,某一门课的学期论文题目,选了汉代王逸的《楚辞·天问序》来自讨苦吃。遇到文学院的吴企明先生,问我近日忙些什么,我就“呵壁”、“问天”地大诉其苦。吴先生是苏州人,研究唐代文学的,一口吴侬软语,平时连上课也不肯说普通话,害那些外地来的学子们吃足苦头。“馁(你)去寻《楚辞解故》来看看,朱季海先生写咯,朱老学问呱呱叫,章太炎先生个得意门生,鲁迅先生个同门,俚人就落了苏州,就是《楚辞解故》不晓得馁阿读得懂”。
等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薄薄一本《楚辞解故》借到手时,才知道上了吴先生的当。天地良心!《楚辞解故》我怎么可能读得懂呢?别说我读不懂,恐怕整个文学院也没几位老先生能读懂。因为这本被誉为“学界天书”的小册子,是以楚语解楚辞,世所少见,正经比屈原的《天问》还天问啊。当时心里就嘀咕,最合适的读者,怕是非语言学家王力先生莫属了。后来才听说,谁能把朱季海这本书看明白,谁就已进入中国楚辞研究前列了。
我把《楚辞解故》像烫手山芋一样还掉,但从此记住了朱季海这个名字。可等我真的见到朱季海本人时,却又有眼不识金镶玉。
那次是在小马师兄家玩,那时小马师兄还住在钟楼附近一条小巷子里,一间平房,正对着一个布满青苔的天井小院。师兄也是个散漫随意之人,跟他一起喝茶聊古籍版本,时间“嗖嗖”地就过去了。然后就有一老者,在门首探头探脑,形迹可疑。师兄见了,走过去招呼他。老者看我一眼,嗫嚅道:“啊,你有客人呀,我等等再来”,语未毕,人已飞速消失。
我问师兄刚才那个鬼鬼祟祟的家伙是谁,很像是来借钱的。“朱季海啊,你不认识他?江湖上名头很大的”,师兄听见我的评语顿时跌足狂笑,“我一定要把你这句鬼鬼祟祟转告他”。
“朱季海?《楚辞解故》!”我飞奔而出,可是哪里还有什么人影?
后来一次是在校门口的“望星桥”堍,小马师兄和他的忘年交朱季海坐在卖生煎包的铺子外面,一条乌黑油腻的长凳,一老一少两个顽童,大有风尘隐士的模样,在午后的阳光里聊得正开心呢。我骑车经过他们时,师兄冲我招招手,诡诡一笑。我深怕我的出现提醒师兄转述那番“鬼鬼祟祟”的评语,于是把脚踏车踩得跟风火轮似的,一溜烟远了……
回到文怀沙大师的年龄,果然,94岁高龄仍不愿被体制招安的朱季海第一句话就说,“追问年龄是一种恶习,这是连小女孩都懂的事。我们认识几年了,我也不知道你年龄,这有什么关系呢?”他这番话是对追问他的傅奇说的,几年前傅奇在苏州城里办了所“复兴私塾”,请朱季海当顾问,又是一个醉心古典文化的“痴子”,呵呵。
傅奇的文章在这里,如有兴趣大家自己看吧。
94岁高龄的朱季海先生
倒是另有一篇好文要借此机会全文转贴,那是俞明的《痴子》,写朱季海写得入墨三分,网上绝搜不到(当然,今天之后可以google到豆腐庄来了)。几年前我曾为美东一家周报客串一个文化版的编辑,为了介绍朱季海,从藏书中找到这篇《痴子》,一个字一个字敲键盘,打字打到手脚发软时,过去的一点一滴重回眼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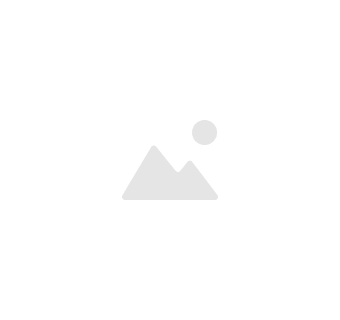

作者:俞明
1906年6月间,日本东京的一批中国留学生和爱国华侨举行欢迎会,应邀赴会的章太炎先生发表了演说,其中有一段话说:“大概为人在世,被他人说个‘疯癫’,断然不肯承认……独有兄弟却承认自己是‘疯癫’。我是有‘神经病’,而且听见说我‘疯癫’,说我有‘神经病’的话,倒反格外高兴。为什么缘故呢?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到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的人也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
苏州人对一些有点神经兮兮的,称做“痴子”。苏州人自以为温文尔雅,对凡是看不惯听不惯的言行,动辄戴上“痴”的帽子。野里野气的女孩叫“痴囡”,调皮顽劣的男孩叫“痴官”,行为怪异的则斥之为“痴头怪脑”。当时有些人便背地里把章太炎先生唤做“章痴子”。太炎先生仙逝后若干年,他的一个关门弟子,一个有大学问而性情古怪的朱季海先生,也被苏人冠以“痴子”的美称。
朱季海不仅是太炎先生的关门弟子,而且是先生最得意的门生之一。1933年初春,春寒料峭,年方弱冠的朱季海在苏州大公园对面律师公会门口看到一张特邀太炎先生讲学的海报,入场券大洋三元(那时一个小学教员的月薪为大洋六元)。朱季海当年是东吴附中高一学生,且是唯一免修语文的学生。他的语文老师认为其国文程度已远远超过高中语文所能给予的。比如,小小年纪的朱季海对《章氏丛书》里晦涩难懂的文字已能侃侃评说。自然,朱季海不愿放弃这次面聆教诲的机会。这样,当这位身穿青竹布长衫的青年正襟端坐在国学讲习班里时,周围的同窗莫不投以惊诧的目光,盖其时数十位听课者,全系中老年国学研究人员,如东吴大学教授王佩诤便是风雨无阻每课必到的,讲习班的主持人是李根源老人和金松岑先生。太炎先生在台上开讲,发现台下竟有一青年在,不免感到奇怪。当时的中国,章太炎声望赫赫,正如侯外庐先生后来评说的,他是近代中国学术史上“自成宗派的巨人”。早年在日本东京,太炎先生就曾为鲁迅、许寿裳、钱玄同等专门开班授课小学。他在小学、经学、史学、诸子学等方面的造诣,到了晚年已臻化境。他的一些弟子如蕲春黄侃季刚,归安钱夏季中(即钱玄同),海盐朱希祖逖先,又如汪东、沈兼士等俱已饮誉海内,卓然成家。他在讲学时,虽庄谐杂出,然博大深邃,旁证博引,如无深厚之国学基础,是听不懂的。某次课前时间,太炎先生特地找朱季海闲谈,不觉浑忘时间,李根源老人两次催请开讲。章太炎在朱季海身上看到了自己年轻的影子。须知章氏在17岁时,已经“浏览周、秦、汉氏之书”,却又“废制艺不为”,不屑仕进,有了与众不同的见地。
不久,讲习班搬至大公园内,讲堂上设一黑板,太炎先生侃侃而谈,引文处背诵如流,作板书之弟子不知所措,常常出现“吊黑板”现象。及至讲《尚书》,先生特嘱朱季海记录,朱用毛笔作书,运笔如飞,讲解处用文言述其意,引文外忠实原文绝少讹误,课毕,稍加修改,即成书稿。太炎先生阅后大悦,乃有意正式收朱为徒。时朱季海正迷恋爱因斯坦学说,有志于自然科学,归家告父,朱父书楼系留日学生,与黄兴、杨度善,素仰太炎之人品学问,力促其子往投名师。于是,1934年春太炎先生定居苏州以后,每天黎明时分,锦帆路50号章宅门前,便见一个着青竹布长衫的青年在等候开门,其时章宅前幢住满了寄宿生,朱季海是通学生。
“章先生早!”朱季海恭恭敬敬执弟子礼,一躬到地。
“呵呵”,太炎先生含糊应着,一边蘸着蝴蝶牌牙粉刷牙,一边打手势叫朱季海去他的书房等候。“季海哪,我昨夜写了一篇文章,想和你商量商量”。从1933年直到1936年太炎先生谢世,这位名重中外的朴学大师对待他的年轻门生亲切有加,常以平等态度和他“商量”学术问题,好似《论语》中的师生问答。太炎先生很宠爱他晚年收授的关门弟子,一天不知要叫多少遍“季海哪!”后人传说章宅当时有“先生派”、“师母派”之分,说师母汤国梨有些嫌弃朱季海。事实并非如此,章宅有前后两进,汤居后宅,不少学生常去后宅请安并呈贽敬,唯独朱季海从未跨进过后宅。汤师母却自有公允之论,她曾喟然叹道:“有些泥水木匠都来拜师了,只有像朱季海这样的人,像个学生子”。
太炎先生大弟子黄季刚,执教中央大学,饮誉海内。朱虽不直黄生活上之失检,但认为黄的治学路子与己相似,对这位师兄的学问甚为钦佩,恨无机缘得识。1935年夏,太炎先生手著《论汉学》上下两卷,交朱誊写后赴宁交黄,有意让自己两个得意门生见见面。但朱抵宁后怪脾气发作,想到黄与己都有恃才傲物的毛病,唯恐话不投机反为不美,踌躇再三,卒未见而返。翠年,黄侃抵苏,太炎先生亲自打电话至朱住所附近之名店“采芝斋”,请转告朱,却因朱外出又失之交臂。是年秋,季刚竟中酒故世,八个月后,太炎先生患鼻菌症和胆囊炎不治溘然而逝。朱季海为治丧招待,季刚之婿来苏吊唁,遇朱,述及季刚生前常在家人面前盛赞季海之才,以缘悭一面为撼。朱闻之大恸,深悔自己的孟浪和狭隘,但朱季海在以后数十年却并未因此而改戒自己性格上的此类弱点。这确乎有碍于他在学术上和人切磋和向人学习。
朱季海一生至今,仅任公职两年,1946年南京成立国史馆,要求馆员须有七年以上大学教授之资历。经师母汤国梨力荐,朱季海受聘去宁。修史时为求翔实,多次风尘仆仆去北平索求北洋军阀史料与清史稿,馆长但植之讽嘲说:“君想做司马温公耶?” 朱大恚,恨声道:“司马亦人,为何不可学?”中国历代史官有骨气的居多,但真正能秉笔直书且又能传世的却不多。朱季海自然不能例外。一日,同事间闲谈,有人告朱,馆长评朱“目无官长”。朱镇目而呼:“此乃长官无目!”他吟唱着“进不入兮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拂袖辞归。他的“初服”便是一衿青竹布长衫。他夹着一只破书包,或在怡园碧螺亭上攻读,或钻进护龙街旧书铺里做“书毒头”(苏州方言,意为书呆子),或去悬桥巷口“九如茶馆”内授徒。
这茶馆讲课也是苏州当时的风尚,当时社教学院的教授也有带着三、五学生“孵茶馆”,边嗑瓜子边讲学的。朱季海私人授课,“九如茶馆”里的跑堂对这位老茶客特别照顾,专门留一张桌子给“书毒头”,朱季海就靠着这点微薄的束修,度其清贫的苜蓿生涯。朱季海的思想体系和观念形态,思维方式和知识结构,被时代风云绞得复杂而凌乱。他在旧时代循着太炎先生的足轨行进,却不能有章氏在政治上多姿的际遇。他可能成为一个纯粹的学人,但他恰恰处在近代史上变化最多的交叉点上,他的传统思想和人生哲学使他对眼前发生的种种变革不知所措。到了新社会,他就象一面古筝置身于现代化的舞台。铁质朱漆,形若云霞,音韵铿锵,有如龙吟,若幽斋独对,屏息以听,则烟波苍茫,木叶萧寥,令人飘然欲仙;但夹杂到摇滚舞曲中,台下是跺着脚吹着口哨的听众,它的存在价值连同精妙的律吕全被震耳的打击乐器淹没。解放后,他的茶馆授徒生涯被迫收摊,学生们纷纷投身革命,但朱季海却茫然四顾,无路可走。他不愿去参加什么革命工作,也不愿到学校去正式执教,他拒绝了市政协的邀请。解放后的数十个寒暑,他坚持他固有的落拓不羁的名士生活方式。50年代初,江苏师范学院顾树森教授完成了名著《中国古代教育制度》初稿,慕朱之名,移樽就教。朱讲明校对一遍须酬金三百,校对后指出百余处谬误,顾再三称谢。其时顾与海上名士时相酬酢,一次在席间谈及朱之学问和生活情况,一客当场解囊五百相助,顾返苏后将款项送去,朱慨然笑纳,竟不置一“谢”字。南京师大某教授于朱季海生日邮寄百元“为先生寿”,朱竟无一字作复。有人问起,朱淡淡说:“收到了”。
在十年浩劫期间,朱季海还算幸运,只在初期饱受一场虚惊。一天在怡园,冲进一批红卫兵,将下棋的、吃茶的、玩鸟的一网打尽,其中就有在碧螺亭上读书的朱季海。这时的朱季海的穿着已时代化,头顶解放帽,身穿退色的蓝卡其中山装,手执宋版书一册,小将们一手夺去,发现其中有好多圈圈三角,不禁大喜,以为抓获了一个身藏情报密码本的特务,立即当场批斗勒令交代。朱结结巴巴解释不清,被口号声搅昏了头,幸亏茶客中多人证明,其人是有名的“书毒头”,手里拿的是音韵书,红卫兵这才网开一面,朱季海方得抱头鼠窜而去。从此,朱季海躲进小楼成一统,不问世事,居然成了当时发烧社会上一个独特的隐士。这多亏“书毒头”、“朱痴子”的名声救了他,使他得以躲开政治雷达的扫描。这一次,水面上的风暴没有摧毁他,却使他沉溺到了湖底,被世人遗忘。他生活无着,典书卖物,每天烧饼油条,中午踅入小饭铺午餐,一角钱一碗鸭血汤,三两米饭,真是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依然故我。人不堪其忧,他却不改其志,乐在书堆中。如是,他熬过了难熬的十年。
粉碎“四人帮”后,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遣专人两度来苏延聘朱季海去宁任教。朱的傲岸脾气又大发作。他以为如若真有诚意,校长应该亲自前来才合乎礼仪,“吾未闻欲见贤而召之也”,“欲其贤人而不以其道,犹欲其入而闭之门也。夫义,路也;礼,门也”,因而他故意提出出种种不合理的要求来难为使者。比如,月薪300元正,多一文不要,少一文不行。虽然这整数不合教授的月薪规定,来人也允承了。最后朱提出一个条件,他上一节课,只有20分钟,并坚持说:“我是没有水份的,20分钟,足够了,足够了!”这是打破大学的教学常规的,使者再三请朱重作考虑,卒不允所请。这样,朱季海仍然吃他的鸭血汤,但不久饭铺店主因鸭血汤利小,改革为卤肉豆腐鸭血汤,价钱一下猛增数倍,这使朱季海大为惶恐,在小饭铺前徘徊趑趄,望汤兴叹。1984年,市某部门负责人在朱同门处得知朱的窘况,商请市博物馆每月补贴车马费40元,领款通知上门,朱竟拒领。后该负责人再三敦请馆长亲自登门送上,朱才“笑纳”。一日,朱与友人路遇此负责人,友人欲相介绍,此负责人力阻,朱亦返身疾行,友人无可如何,笑曰:“此之谓君子施恩勿望报,受恩不言谢也”。
太炎先生《致潘承弼书五》中云:“季刚,繭斋,学已成就,繭斋尚有名山著述之想,季刚则不著一字,失在太秘”。及至黄侃去世,太炎先生在《黄季刚墓志铭》中写道:“……然不肯轻著书,余数趣之曰‘人轻著书妄也,子重著书吝也’……岂天不欲存其学邪?”由是观之,大学了问家著述也不一定很多。黄侃一生只写了《三礼通论》和《声类目》。南京师大一位老教授说,“季海先生在音韵、文字、训诂诸领域无一不精,就是不肯把肚里东西掏出来”。解放初期,中华书局熟知朱季海的老编辑三顾茅庐,朱感到盛情难却,动笔写了《楚辞解故》、《南齐考注》和《庄子诂言》三部书,南京师大已故段熙仲教授拜读之余,叹服道:“朱先生之学问诚深不可测!”朱季海后来又为上海美术出版社写过一册《石涛画谱注释》,却是连熟悉他的同门也感到纳闷,不知朱季海也懂画论。那么,朱也能书法么?苏州市多如牛毛的书法家,从未听说过朱季海其人。十余年前,南京师大一位叶教授曾闯入过朱的居室,那是一块禁地,朱的一些熟人从未有过登堂入室的殊荣。朱住的楼上两大间全堆满了书,在书堆中仅一床、一榻、一椅而已,发黑的墙壁上和窗棂上全用毛边纸糊着,叶教授仔细一看,看得眼睛发直,后来悄悄告人说:“那一手行书,不要说苏州,就是当今中国书坛,也是少见的!”朱季海还通晓英、日、德三国文字。他青年时期就钻过相对论等原著。唉,朱季海可算得上是一等学问家了,但就是缺少一门学问:处世学。
“什么大学问,嫁仔俚末,吃仔一世苦!”朱师母说。多年来她早已拒绝料理朱的生活了。她是一个刺绣工,并不了解朱。她说的话是实在的。
“一个痴子,一个书毒头”,邻居们简捷地评说。这种评价已有40余年历史,他们观察了这么多年,可谓秉笔直书。
“学问呢,我不如他,但他实在脾气太坏了,太坏了!”一位很有点名气的同门师长说。这样的话在同门中富有代表性。
“哼!”年逾古稀的朱季海才就着萝卜吃过两碗泡饭,反剪双手在书堆间踱步,他吟哦道:“知前辙之不遂兮,未改此度。车既覆而马颠兮,謇独怀此异路。”
(见俞明散文集《姑苏烟水集》,原载《瞭望》1989年第26期)